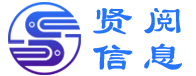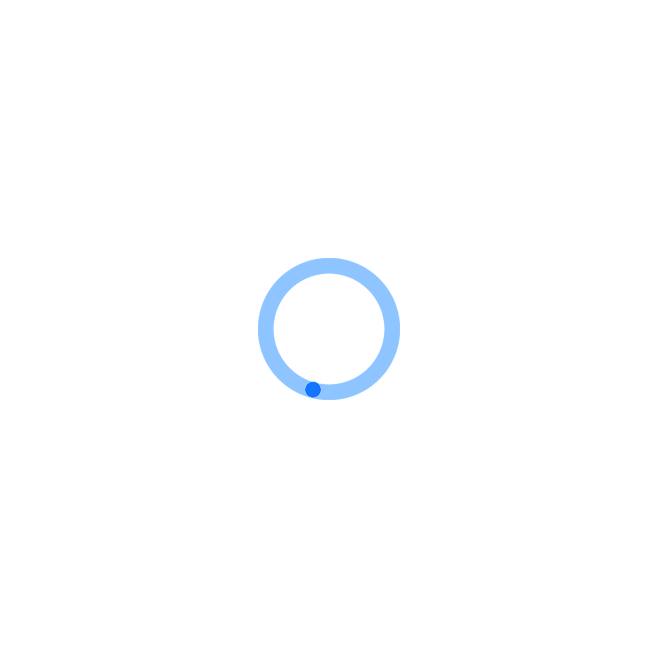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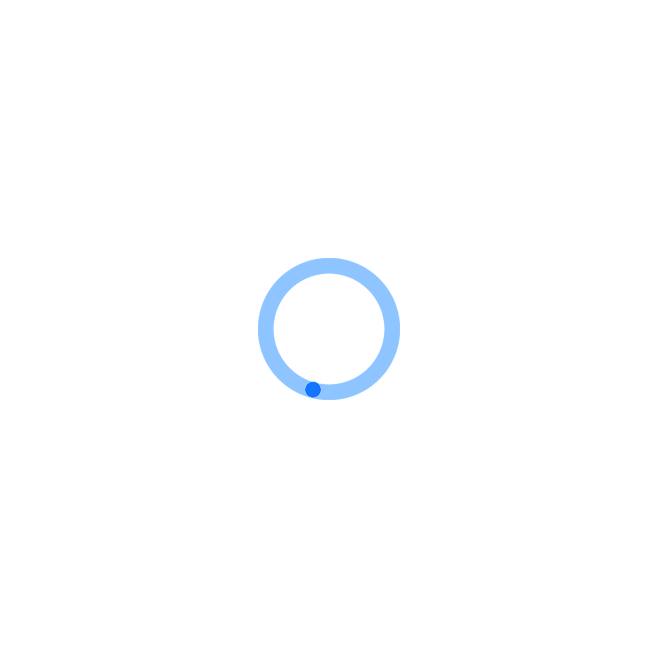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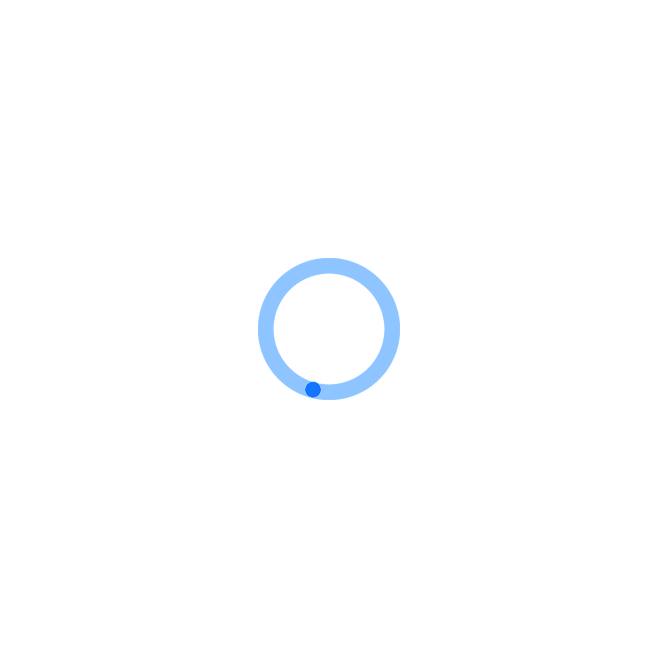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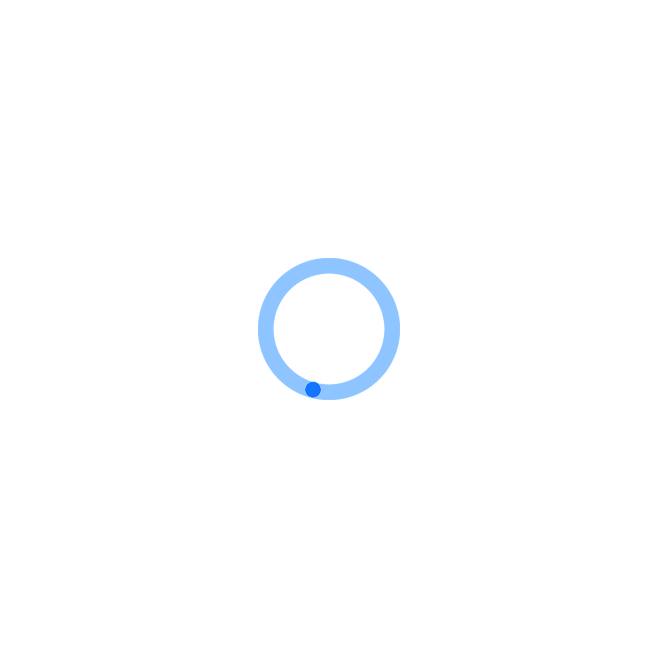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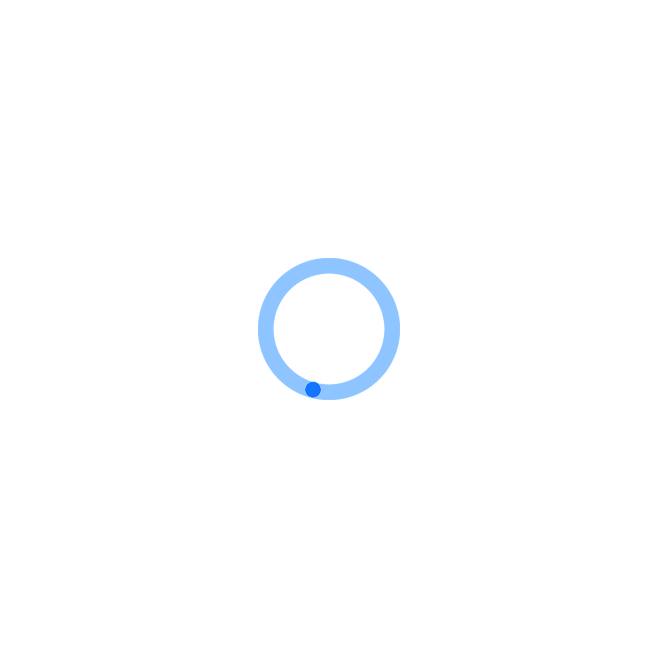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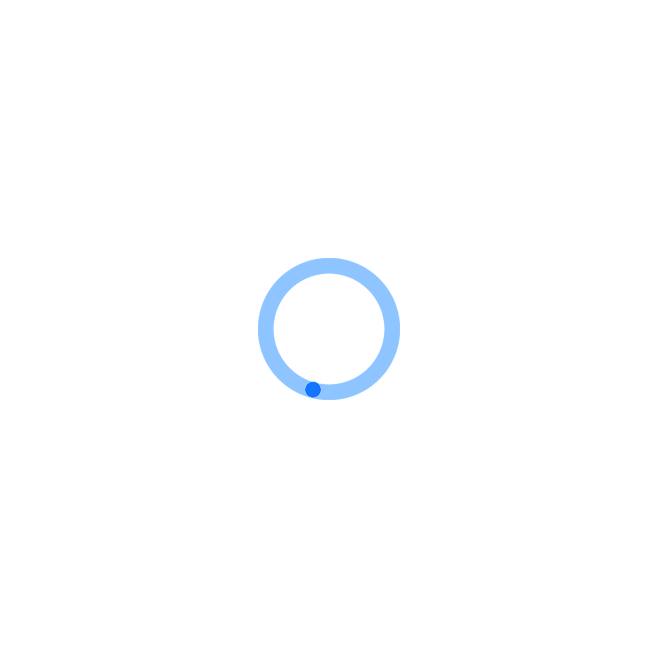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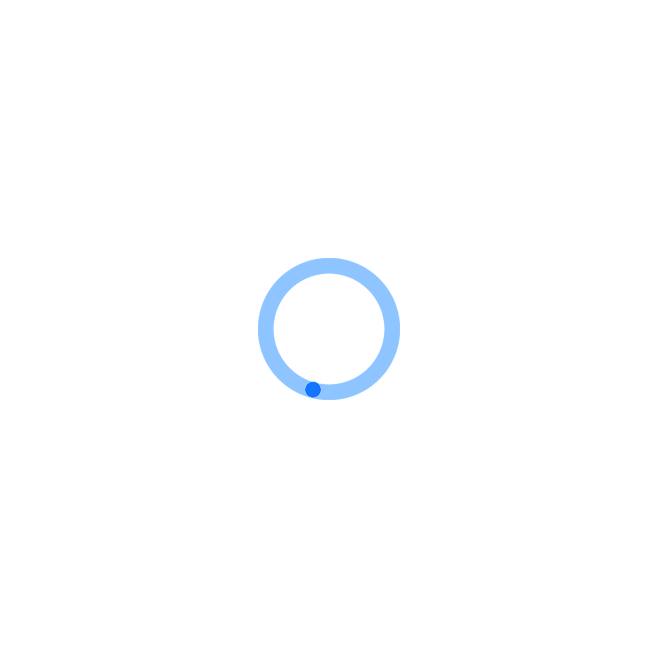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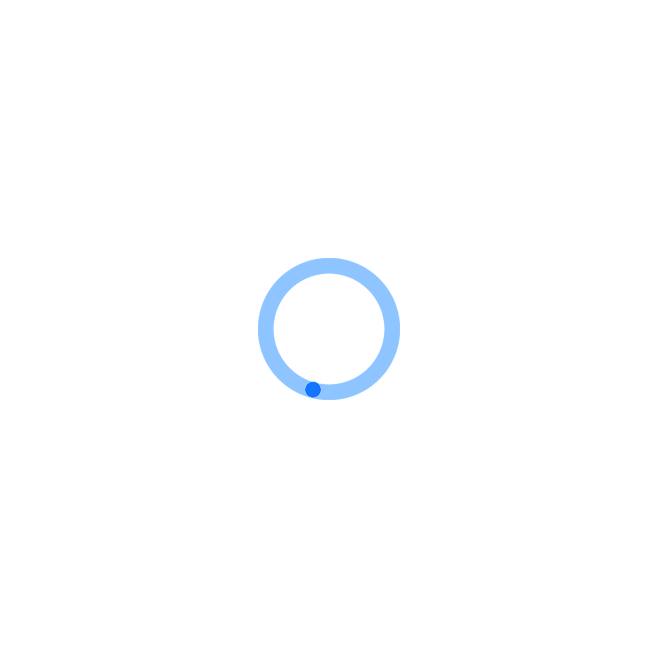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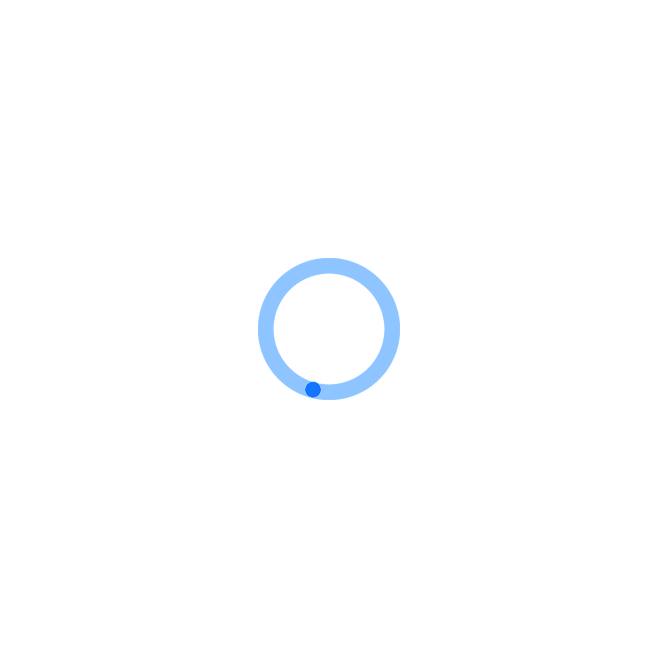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还剩7页未读,继续阅读
文本内容: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个人”观念的辨析作者:汪卫东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4期摘要《摩罗诗力说》作为鲁迅早期系列文言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心声”-“新声,,、“诗”和“诗力”等一系列关键观念的标举与阐发,在“精神”之后,又为以“立人”为核心的“第二维新之声”提出了一个“诗”一一文学的契机,这些观念及其阐述理路,构成了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关键词〕“心声”一“新声”“诗”“诗力”“第二维新之声”〔中图分类号〕T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4-0097-06《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日本时期系列文言论文中的一篇,作为系列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心声”和“诗力”的强调,为其首倡的“立人”思想提供了一个“诗”一一文学的契机,通过对该篇理路的仔细梳理和辨析,当能进一步考察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内涵该篇始于申述“心声”的重要在鲁迅的描述中,“心声”与民族兴亡息息相关“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口同绝;且复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末页矣……英人加勒尔Th.Carlyle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Alighieri,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扎尔,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然则何为“心声”?中国古语云“言为心声”,又云“诗言志”,从而把“心声”与“诗”直接沟通起来;“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C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口同绝;且复曼衍,视其种人”直接承上句之“心声”而来,在上下文关系中,此句之“诗歌”应该是指上句的关键词“心声”,“心声”即“诗歌”,但可以看到,在鲁迅那里,“诗”所“言”者非来自“志”,而是直接来自原初的“神思”在《科学史教篇》中,“神思”是作为“科学”源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这里,仍是强调它的原初性,此“神思”与生俱来,故鲁迅在第二段开始即引尼采说“尼怯(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狡獴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此处所引“新力”,与前几篇论文所言之“人类之能”、“意力”,皆是人本然所具;这里第一次出现“隐曜”这个词,即后来在《破恶声论》中出现的关键词“内曜”之“曜”,与“神思”一样为人性中所固有鲁迅首先提出“心声”的概念,并把它和“神思”、“隐曜”、“自觉”等概念相互沟通,“心声”来自人本有之“神思”和“隐曜”文章的开始两段,首先提出上举诸观念,但其所要表达的是,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古民之心声手泽”虽曾“庄严”与“崇大”,然已“不通于今”,现状是“心声”蒙蔽,“恶声”喧嚣,故作者深深感叹“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来袭”既然“心声”与家国存亡如此攸关,该于何处寻觅“心声”?既然中国古代曾经“庄严”、“崇大”的“心声手泽”已“不通于今”,则只能“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至此,“心声”过渡到“新声”,“心声”一“新声”在鲁迅的阐述中连为一体然则何为“新声”?“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生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牙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的“新声”,来自“摩罗诗派”,“摩罗”,是梵文Mara的音译,指佛教所说的魔鬼从鲁迅所列的“摩罗诗派”的谱系来看,则所谓“新声”,是发源于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并在十九世纪蔚为大观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诗潮,鲁迅悬置了摩罗诗人的历史特征,把“新声”归结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可见他所垂青于摩罗诗(“新声”)的,是其具有“反抗”精神并诉诸“动作”,因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和巨大号召力的一面鉴于中国“诗人绝迹”、“心声”衰微,鲁迅欲以“异邦”的“心声”一一“新声”来启示、激发国人的“心声”在鲁迅的描述中,“新声”的价值建立在进化论视野中的社会进化观,在进化论视野中,“人间”与“人事”的本质,不是“平和”,而是“战事”,并时刻隐臧着“杀机”作为这一事实的反面,鲁迅着重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逆进化的历史观和“不攫人心”的退守倾向“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称“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进而直接批判以老子为代表的无为退守的思想“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攫人心;以不攫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攫人心”之说,原出《庄子•在宥》“汝慎无攫人心”,《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攫宇”成玄英《疏》“攫,扰动也”,嵇康亦有“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章太炎亦以“攫宁”相对“攫宁而相成,云行雨施,而天下平”(《蓟汉微言》)然而,人间世界的事实是“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鉴于这一事实,鲁迅最后说“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被鲁迅当作科学真理接受的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残酷事实,在这里被移植到民族国家之间,成为二十世纪民族国家“争存”于世界的一个普遍规律,“摩罗宗”之可贵,就在于面对这一人世的“可悲”,而张主义无反顾的“反抗”和“动作”,这是争存于这一残酷世界的唯一选择,“摩罗诗”和“新声”的力量,就在于实施于动作的反抗式生存鲁迅进一步指出,逆进化而行的“不攫人心”倾向也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理想中对此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前述“中国爱智之士”的正面主张,而是直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卑下利己动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攫,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攫人,或有人得攫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攫我,或有能攫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鲁迅由此联系到柏拉图理想国对诗人的驱逐,转入对诗人之所以能“攫人心”的解释“盖诗人者,攫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诗”成为人人所共有的人性中的本然存在,也是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的人性基础,只是“诗人”早感之并能言之,在此“诗性论”基础上,诗人成为极具号召力的人物鲁迅痛心地指出,中国的“诗人绝迹”,一方面是由于有意的压制,另一方面则是民众的诗心自蔽“人人之心,无不湖二大字日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攫之?夫心不受攫,非槁死则缩月肉耳,而况实利之念,复炎占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崽,无古民之扑野,有末世之浇漓,又必然之势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即间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创痛少去,即复营营于治生,活身是图,不恤污下”卑下之“实利之念”遮蔽了“诗心”的萌发,与《科学史教篇》所言“实利”对“神思”的遮蔽同作为对照,文章又举普法战争中德国诗人阿恩特和柯尔纳以诗歌激发国民起而反抗拿破仑的故事,“故推而论之,败拿坡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在鲁迅的解释中,民众的“诗心”与家国的兴亡密切相关,若“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则诗人只需振臂一呼,即可引起国民诗心的共振,发为不可摧折的反抗之力鲁迅似乎忽然意识到过多强调“诗”与国家兴亡关系的不妥,转而申明“然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强调“此篇本意,固不在是也”于是,下文转入对“文章”价值的讨论鲁迅对文章价值和用途的强调,首先运用的是否定法和排除法,“文章”的“本质”是使人“兴感怡悦”,所以“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然而,“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因为,“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句力,有时丧我而徜徉,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鲁迅运用了庄子式的语言称之为“不用之用”,并最后进一步明确“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这里所说的“文章”,沿用了自汉开始的“文章”与“文学”二分法,此“文章”意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诗在现代文体的分类中,乃文学之冠冕在鲁迅的描述中,“文章”之用不是直接作用于知识(“益智”)、道德(“诫人”)和实利(“致富”、“功名”)等具体效用,而是作用于这些具体效用之外,与人生之情感(“醇乐”)和“理想”相关,最终,“文章”之“职与用”即“涵养人之神思”如前所述,“神思”在鲁迅看来是内在于人性而人人所共有的,并且是人类一切创造(包括知识、实业)的最终源泉,由此可见,以“涵养神思”为“职与用”的“文章”,其作用比上述各种具体效用更为根本鲁迅还指出了“文章”的另一“特殊之用”“此他丽于文章能事者,犹有特殊之用一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鲁迅以比喻来说明这一功效“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直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视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囊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冰”之喻强调的文章不涉理障、直抵人心的功能,其功效特点是快速与强烈,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达到效果同时,鲁迅引亚诺德(M.Arnold)之言,谓“诗为人生评鹭”,称“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强调的是文学与人生的直接关联及其教诲启示作用,但又强调“其教复非常教”,即与宗教、道德之“教”不同,而是直接诉诸自身的“自觉勇猛发扬精进”此处对文章神奇效用的描述,可以见到鲁迅以文学启蒙的思想依据;与此相联系,鲁迅在下一段着重批驳了“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的文学观“要在文章与道德之相关谓诗有主分,日观念之诚其诚奈何?则日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得诚奈何?则日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联系上文鲁迅所言“文章”启示“人生之诚理”,则“据群学见地以观诗”之“诚”与前者应属不同“诚”作为一个古汉语词,曾是传统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大学》讲“诚意”,《中庸》中,“诚”成为本体性的核心概念,被理解成先天的原则,人的本性,故日“反身而诚”我们知道,“诚”也曾是鲁迅口本时期的重要观念,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缺少的就是“诚和爱”,他对“心声”和“白心”的看重,即与对“诚”的期待相关,终其一生的对虚伪国民性的批判,亦可从反面看到他对“诚之品性的器重鲁迅对“群学”之“诚”的批判,针对的应是对“诚”的僵化的、道德化的理解此处对“文章”一“诗”的价值及其功用的辨析和强调,可以说是鲁迅版的“诗辩”在西方诗学史上,发生过几次对诗歌的辩护,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辩》雪莱对诗的辩护基于对想象力的神奇力量及其作用的阐释之上,他认为,想象力是人类及其社会保持生机的活力源泉,没有想象力,社会就会哀败和枯竭,而诗产生于人的想象力,并作用于人的想象力,使人保持一种活跃的、生动的和创造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之中包含着人的最高的善的道德,从而增进人类的福祉在诗歌消失的地方,就是想象力枯竭的地方,在一个僵化停滞的社会中,需要诗歌激发想象力的源泉,以形成变革社会的力量诗人,作为想象力的富有者和激发者,被雪莱授以“世界非公认的立法者”的空前崇高的地位⑴可以看到,鲁迅对“诗”的强调也是建立在对“神思”一一想象力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也许意味着鲁迅的“诗辩”受到了他所钟爱的雪莱的影响;但还要看到,鲁迅的“诗辩”中又可以找到中国传统的诗学思想资源,如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以及在韩愈那里明显表现出来的把社会危机的解决诉诸文章改革的习惯方式;雪莱和鲁迅都是在“诗”的价值受到漠视的时代氛围中起而为其价值辩护的,雪莱所面临的是理性霸权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全面统治以及社会体制僵化造成的对人类想象力和新的生机的压制,因而以“诗”为契机重唤人的精神潜力;鲁迅“诗辩”的背后,是晚清知识界在危机中反思中国之学“文胜质”的普遍思潮,以及他所面临的,在这一思潮中形成的重实学轻文学的普遍倾向,这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专业选择的“偏科”现象中可以一目了然,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的举措,可以说是针对整个时尚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叛逆行为,而这一惊世骇俗之举的依据,在这一“诗辩”中正可以找到鲁迅在申说了“文章”之“不用之用”后,介绍了所要介绍的“摩罗诗人”系谱的第一位诗人拜伦的“撒但”称号的由来,以及“撒但”在西方宗教中的意义及自己的重新解释在鲁迅的解释中,“撒但”实为人类的祖先,如果没有“撒但”的诱惑,就没有人类的产生,“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而现在的人是“挪亚子孙”,他们于大洪水后劫后余生,“自必力斥抗者,敬事主神,战战兢兢,绳其祖武,冀洪水再作之日,更得秘诏而自保于方舟耳”因而,现在的人类皆是上帝的顺民,而所谓“撒但”者,鲁迅用生物学的“反种”反祖现象加以解释其实,可以看到,鲁迅对“撒但”的解释,其根据之一正是他在后文着重介绍的拜伦的《天和地》Heaven andEarth由“撒但”的释义转入对摩罗谱系的具体介绍,从拜伦始,中经雪莱、斯拉夫民族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沃瓦茨基、克拉辛斯基,最后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作结据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考证,《摩罗诗力说》对诸多诗人的介绍,几乎都有材料来源,而且大部分是直接转译过来的,北冈对此有极为细密、严谨的爬疏、辨析和考证晚清时介绍新学的文章往往是来自外来材料的客观转述和出自自我的主观评价纠缠一起,很难分清,《摩罗诗力说》正有这一晚清时期的普遍特征,鲁迅把诗人的行状、作品、传播及叙事者的解释及评论结合在一起,整合进“摩罗诗力说”的宏大叙事中,因此在整体上还是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式,北冈也断定“《摩罗诗力说》是在鲁迅的某种意图支配下,根据当时找得到的材料来源写成的”
[2]⑵其考证的目的就是“将材料来源的文章脉络和鲁迅的文章脉络加以比较检查,弄清鲁迅文章的构成情况,就可以从中领会鲁迅的意图”
[2]⑵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考察,应不要局限于这些材料本身,而要看这些材料的“拿来”是如何受鲁迅主观意图所支配并如何服务于这一意图的鲁迅的介绍部分篇幅很长,为了避免梳理过程的漫演,笔者拟对这部分的文本作有侧重点的处理,即抓住鲁迅介绍过程中与所利用材料资源的差异,把捉其主张和意图所在据北冈考证,《摩罗诗力说》第
四、第五节有关拜伦部分的材料主耍来源于木村鹰太郎的《拜伦一一文艺界之大魔王》鲁迅对拜伦的介绍,主要是结合其生平和作品而从他选择的侧重点的不同,可以见出他的一些倾向和意图鲁迅主要介绍的拜伦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海盗》、《曼弗雷德》、《该隐》,而着重介绍者为后三篇虽经北冈考证,鲁迅介绍《海盗》的文字,大都可在木村那里找到对应的表达,但可以感到,鲁迅的重述,渗透了自己强烈的感情,至少说明,北村的这方面介绍曾深深地打动了他,如“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孤剑轻舟,所向悉如其意”、“故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权力若具,即用行其意志”、“然康拉德为人,初非元恶,内秉高尚纯洁之想,尝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比见细人蔽明,谗陷害聪,凡人营营,多猜忌中伤之性,则渐冷淡,则渐坚凝,则渐厌弃;终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这里突出的是康拉德的以强大意志为根基的复仇精神,对康拉德由爱心转向厌世和复仇的描述,与鲁迅二十年代所心仪的绥惠略夫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极为相似,而相同的体验,在他后来的心路历程中,也几乎经历了一回鲁迅后来所受影响说明,康拉德的强大个人意志及其复仇精神,是他当时极为钦佩和认同的;对于《曼弗雷德》的介绍也是这样,鲁迅着重突出的是曼弗雷德秉持个人意志、虽绝望厌世而反抗不止的形象“一曰《曼弗列特》(Manfret),记曼以失爱绝欢,陷入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见形问所欲,曼云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则对日,死果能令人忘耶?复衷疑而弗信也”“意盖谓己有善恶,则褒贬赏罚,亦悉在己,神天魔龙,无以相凌,况其他乎?曼弗列特意志之强如是,裴伦亦如是”在对《该隐》的介绍中,鲁迅主要突出了卢希飞勒与该隐关于神的善和恶的对话,对传统的善恶道德予以质疑,“卢希飞勒不然,曰吾誓之两间,吾实有胜我之强者,而无有加我之上位彼胜我故,名我曰恶,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加了一段木村所没有的卢希飞勒善恶观与尼采善恶观的比较此其论善恶,正异尼怯尼怯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行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谥故尼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通过比较,鲁迅在肯定“图强”的共同点时,把二者关于善恶与强弱的关系区别开来,参照后文有关拜伦相关立场的比较,应该说鲁迅赞同的是卢希飞勒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在介绍了《天地》中的关于诺亚子孙的议论后,鲁迅有一大段不见于木村材料的发挥然人竟无惭也,方伏地赞颂,无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强使众生去而不之理,更何威力之能有?人既授神以力,复假之以厄撒但;而此种人,又即主神往所殄灭之同类以撒但之意观之,其为顽愚陋劣,如何可言?将晓之欤,则音声未宣,众已急走,内容何若,不省察也将任之欤,则非撒但之心矣,故复以权力现于世神,一权力也;撒但,亦一权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顾其制众生也,即以抗敌倘其众生同抗,更何制之云?裴伦亦然,自必居人前,而怒人后于众盖非自居人前,不能使人勿后于众故;任人居后而自为之前,又为撒但大耻故这段话对“撒但”和“众生”复杂关系的揭示,堪称体察入微,他传达了鲁迅所体验的先驱者对民众的复杂情感,这一情感体验,在二十年代中期的绝望中的鲁迅那里有更为多的表达日本时期的表达,说明这一纠缠鲁迅的矛盾,从他的思想起点处就已开始,而且体验已经非常深刻,这大概是鲁迅的一个极为独特的地方正是在对“撒但”充分同情的基础上,鲁迅强调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日,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强调拜伦的“压制反抗,兼一人矣”,与上文卢希飞勒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同值得注意的是,“压制反抗,兼一人矣”与“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都是鲁迅自己的话对于拜伦生平行状的介绍,主要集中于拜伦援助意大利和希腊独立的行为鲁迅对拜伦助希腊独立行为的重点介绍,不仅是为了强调其“所遇常抗,所向必动”的精神,而且突出了拜伦以自身的强大扶助弱小的一面在鲁迅的描述中,拜伦援助希腊的行为是在“自由”和“人道”的信念下作出的,这一行为已经超越了一己民族的界限,和《破恶声论》中对“兽性爱国”的批判结合起来,可以看到鲁迅既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又超越了一己民族的局限,具有世界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取向对“希腊人民之堕落”及其“国民性之陋劣”的指责,“自意振臂一呼,人必靡然向之”、“盖以异域之人,犹凭义愤为希腊致力,而彼邦人,纵堕落腐败者日久,然旧泽尚存,人心未死,岂意竟情愫于故国乎?”、“特至今兹,则前此所图,悉如梦迹,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者如此也”这些木村材料中没有的话,都能在他日后文章中看到相似的痕迹所可注意者,在转述木村关于自尊之人与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加上“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一句话,突出了自尊之人与厌世的关系,这一强调,几乎是对鲁迅小说中以魏连殳(《孤独者》)为代表的厌世主义者的准确解读最后对拜伦的总结是“吾今为案其为作思维,索诗人一生之内鼠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即强调其自尊、尚强、无畏,具有强大的反抗意志并诉诸实行的精神,而且,其反抗不是侵凌弱小,而是为了“独立”、“自由”和“人道”联系前文的“压制反抗,兼一人矣”与“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等鲁迅自己的评价,可以发现,鲁迅尤其强调拜伦自强而同情弱者,以“自由”、“人道”作为自身行为准则的一面,这大概就是他后来在《破恶声论》中所极力张主的与“兽性”形成对照的“人之性”北冈注意到这一点,她指出鲁迅也和木村一样高度评价拜伦的反抗精神,但具体内容却有重大差异木村认为暴君和反抗者在哲理上是相同的,但鲁迅却在根据木村文章说的“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之后,指出,“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人道”,不是引用木村的著作木村由于礼赞强者,蔑视弱者,所以认可“将万物作牺牲”,“将无数苍生作自己欲望之垫脚石”斗争,与此相反,鲁迅却认为拜伦的反抗是为人道而战斗所谓“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成为鲁迅评价拜伦的基干,它也是《摩罗诗力说》中一以贯之的思想鲁迅没有从肯定优胜劣败必然性的强者理论出发蔑视弱者[2]⑷又说然而,仔细观察他们描绘的拜伦的英雄形象,就会看出鲁迅笔下的拜伦具有人道主义色彩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鲁迅这样直截了当地阐明了人道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用的几段,都没有材料来源,而是鲁迅自己的话[2](4-5)北冈还注意到鲁迅对木村所涉及的拜伦的快乐主义和与女性的关系的材料并不留意甚至作了割舍“没有涉及木村提到的《沙达那帕拉斯》和《唐•璜》,关于《海盗》,只介绍康拉德惊人的复仇精神,而略去康拉德对妻子美多拉的深深爱慕[2]⑷联系前文所指出的鲁迅对施蒂纳唯我主义的利己和享乐倾向的隐忧,则可以判断此处显现的倾向与他的超越一己之利益的“个人”观念相通,而这,正是他钦佩拜伦利他的人道主义的原因确立拜伦为摩罗诗宗后,鲁迅以拜伦的精神倾向为线索,逐一介绍了修黎(雪莱)、普式庚(普希金)、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密克威支(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斯沃瓦茨基)和裴多飞(裴多菲)等诗人,雪莱与拜伦同为英国人,后五者分别来自俄国、波兰和匈牙利,都属斯拉夫族,鲁迅就此把拜伦的精神线索引向别国(尤其是斯拉夫民族),展示并梳理一个摩罗诗人的精神谱系最后,鲁迅总结道“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强调的是他们有诚心、有坚强的意志,反抗世俗,并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唤醒民众,最终使自己的民族得以振拔兴起这是对摩罗精神的一次概括鲁迅如此热情地介绍摩罗诗人,并突出其摩罗精神,立足点还是在国内,反观自身,不禁发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中国由于长期“孤立自是,不遇较雕,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古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氨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中国也”在鲁迅的表述中,中国的问题在于实利和习惯的束缚,这些都需要精神尤其是基于个性的精神的重新振作因此他断定“夫如是,则精神界战士贵矣”并在篇末大声疾呼“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第二维新之声”在中国维新运动陷入困境中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把“异域新宗”和中国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第二维新之声”应着眼于对异域“新声”一一“心声”的引进,以激起沉沦于“实利”和“习惯”的国人心灵“心声”(“诗”),直接来自作为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最终源泉的“神思”,由于“神思”是每个人的生命中所本有,因此人人都有潜在的“心声”(诗),这就是鲁迅说的“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而中国的现状是“诗人绝迹”,“心声”遮蔽,因而国民“元气慧浊,性如沉重,或灵明已亏,沉溺嗜欲”,(《破恶声论》)终造成“苓落颓唐之邦”(《摩罗诗力说》)为激发国民之“心声”,鲁迅引进摩罗诗人刚健有力的“心声”-“新声”从所介绍的摩罗诗人的谱系中可以看到,摩罗诗所表现的摩罗精神,是具有不断超越世俗和自身的强大的意志力量,并具有敢于反抗一切外来压迫的精神,鲁迅所垂青者,就是其中的意志力、反抗力和超越力,以此“诗力”,给萎靡、堕落的国民性注入新的活力,以生命力和精神力的重新振拔,带来邦国的复兴鲁迅以“诗鼓动力以力”激发“精神”,可以说,他的“第二维新之声”所抓住的是“精神”和“诗”-“心声”这两个契机,虽然,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摩罗诗”的介绍和论述没有局限于纯文学范畴的“诗”,但是,对“诗力”的过分推崇第一次明显把中国变革的契机转向对文学领域的关注,应该说,鲁迅对“精神”和“文学”这两个契机的敏锐把握,远接十年后“五四”的风雷对“诗”的强调不仅停留在其感染作用的功能上,“诗”甚而成为人的普遍性的承担者和精神根源的象征,鲁迅的这一“诗学”处理方式,显现出以艺术(“美”)取代道德和宗教功能的一个现代思想倾向,而对于鲁迅自身来说,则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诗学和近代德国美学对他的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此不作详论笔者想指出的是,艺术范畴的“诗”并不能担当他所要委以的重任,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参与了他后来的启蒙危机〔参考文献〕L1]雪莱.为诗辩护[A].伍蠡甫、胡经之主编泗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2]北冈正子著.摩罗诗力说材源考[M].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责任编辑马胜利)。
 个人认证
个人认证
 优秀文档
优秀文档
 获得点赞 0
获得点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