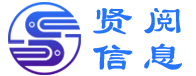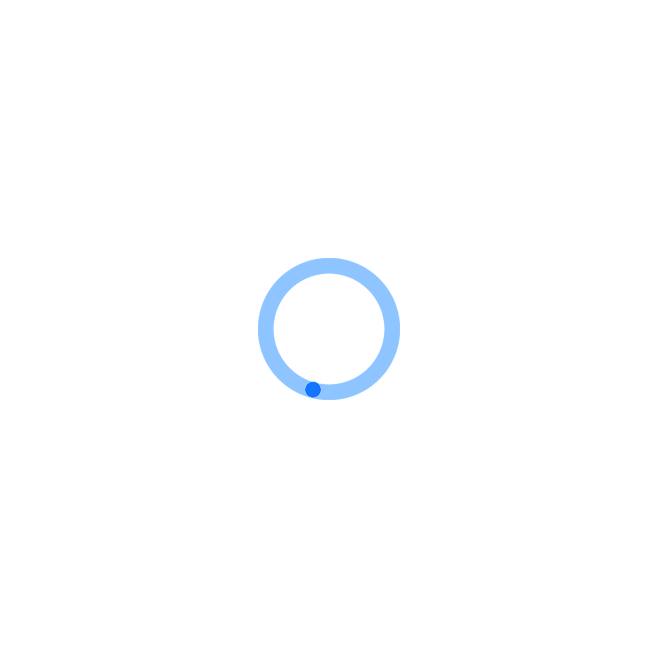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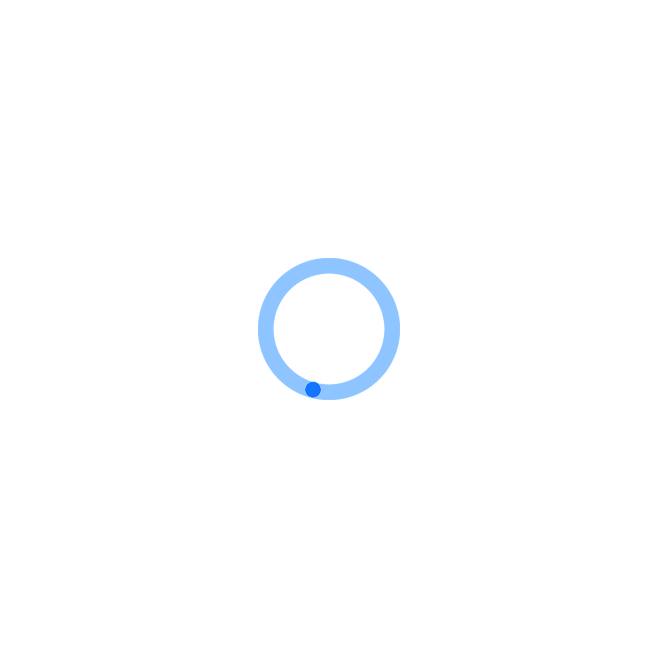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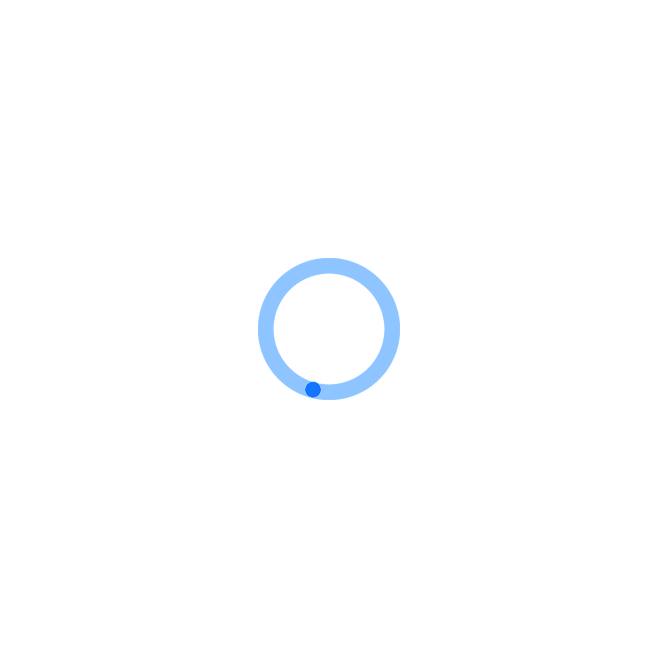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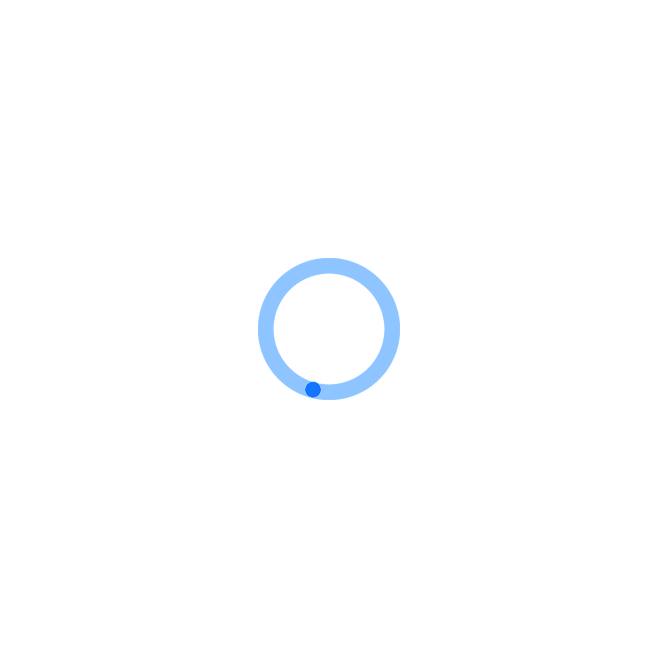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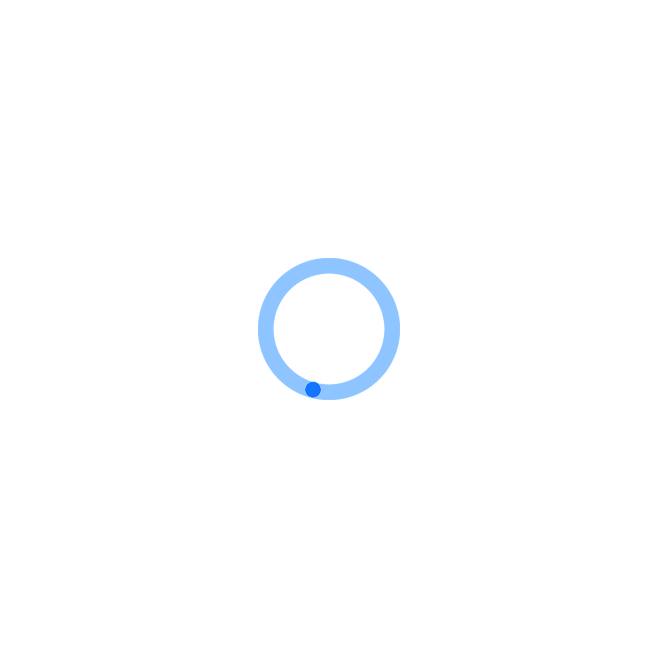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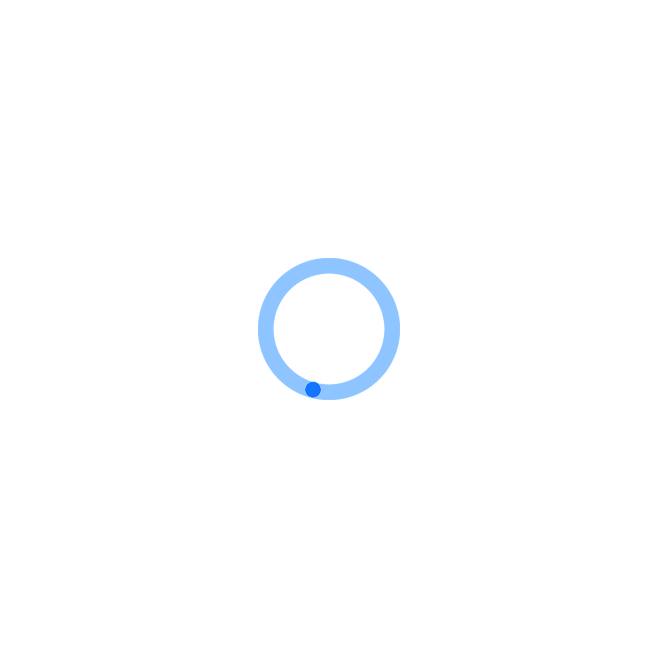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还剩4页未读,继续阅读
文本内容:
空间生产与资本生产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在以传统文明和情感关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真实的劳动、仪式、宗教和仪式生活削弱了人们对空间概念的感知空间(空间)和地方(地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融入当地的时间领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空间脱离了地方的时间层面,直接融入空间的时间层面空间的社会性内涵及其被生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发现了,它既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卡斯特,2001:504),也是“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不同的是,福柯关注的是空间生产的微观政治学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话语在空间向度上的表征智慧和实施过程,即权力如何通过对空间的规训来传递特定的压制关系不得不提的是,福柯的空间规训话语植根于20世纪
60、70年代的社会语境,然而在当下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规训的策略和机制是否呈现出新的生产途径具体来说,以SNS、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建构了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因为福柯特别强调在“可见性”维度上思考空间实践的社会观念史和微观政治学,而社会化媒体又制造了一系列与“可见性”(visibility)生产有关的空间实践和规训景观,这隐隐地指向了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本质所在鉴于此,本文对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进行“再语境化”审视,探讨其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适用性、工作机制及其可能存在的不足这是从空间意义上对福柯规训思想的一次批判与发展,其目的是在新传媒环境下批判性地诠释并反思福柯的空间批评思想
一、权力规训“全景监狱”的缘起如果说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空间在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性意义,福柯则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空间的规训实践及其承载的社会观念史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主要见于《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主要强调权力技术在空间维度上的治理策略和规训实践在《疯癫与文明》
(1961)中,福柯聚焦于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推行的“精神病院”这一空间形态,疯癫之所以从一种自然现象上升为一种有威胁的、不合法的社会疾病,不能不提到权力对特殊空间形态的生产实践和主体规训过程在福柯那里,精神病院实际上是被精心发明的“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福柯,1999:241)空间规训的基本策略体现为三种极为隐蔽的权力技术一一缄默、镜像认识和无休止的审判(福柯,1999:241-249),“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福柯,1999:247)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病人院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福柯,1999:249)正因为精神病院这一空间形态被发明出来,而且进入政治和道德话语的陈述体系和规约实践中,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被建构并生产出来,权力话语最终在空间意义上实现了“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管制”的社会治理目的(福柯,1999:246)如果说《疯癫与文明》强调一种特定的空间形态的生产之于主体规训的决定性意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1975)中则诠释了一种普泛的空间向度上的权力模式福柯突破了传统的权力观念范畴,强调在空间意义上发现并理解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其空间规训思想的基本涵义可以概括为: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权力的眼睛”的管制范畴和规约体系具体来说,福柯借用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on)来揭示19世纪规训制度的权力运作机制“全景监狱”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化的空间构形(configuration)-四周是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只需要站在瞭望塔上“观看”,便可以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全景监狱”虽然是监狱空间的建筑学形象,但福柯则视其为一种普遍的、典型的空间实践模式,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福柯,2003:230)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医院、工厂、学校、机关等社会机构纷纷仿效了“全景监狱”的权力模式和规训策略“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接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福柯,2003:231)进一步审视“全景监狱”的微观政治学原理,它实际上“是一种分解成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福柯,2003:226)在这个特殊的空间装置中,权力话语被分配了最佳的“观看”位置,监视成为一种隐蔽的空间管制策略和主体规训路径,”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福柯,1997:158)福柯进一步指出,空间规训的最终结果就是将现代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因为“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福柯,2003:238),其目的就是“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福柯,2003:240)由于“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空间规训实践变得愈加隐蔽而具生产性,这也是为什么福柯认为空间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形成了一一“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福柯,2003:242)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权力争夺的场所,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空间生产实际上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而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话语的空间化途径实现的话语是一套陈述体系,旨在建立一种“排除的规则”(rule ofexclusion),如医学领域的正常/反常、平衡/失衡、健康/不健康、有用的身体/对社会有害的身体等二元对立话语系统,其目的是“决定何者是该被认知的‘真理、谁有权得知、什么是合法的、谁有正确的位置来应用知识,以排除或驯服不具备知识的对象与客体”(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的权力运作的基础(
二、空间可见性的生产与权力技术的发挥何塞•凡•戴克(社会化媒体的根本使命就是重构社会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人脉网络,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空间的社会化途径(socialization)实现的诸如微博的“周边的人”、微信的“摇一摇”、陌陌的“地点留言”、人人的“人人报道”、遇见的“邂逅游戏”、群群的“随意群组”等社会化媒体应用服务大都致力于发现、激活并搭建空间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在微信的“摇一摇”中,如果两个人同时摇动手机,两个陌生的空间便极具戏剧性地建立了某种微妙关系当一个空间被其它空间所识别、所认领、所发现,它便从其原始的属性和状态中抽离出来,进入社会化的关系网络中,这一过程对应的正是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空间的社会化过程建立在空间的可见性基础上,社会化媒体使得可见性的生产更隐蔽、更彻底、更具生产性在福柯那里,可见性的生产,既是空间规训的方法,也是空间规训的附加产品可见性生产建立在监视机制之上,而监视是一种最常见的官僚形式和约束方法监视的主要后果就是在被监视者身上“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福柯,2003:226),而这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政府”(福柯,2003:227)正因为空间被置于一种公开的、可见的、透明化的监视状态中,对空间的规训和管理才成为现实正如福柯(1997:149)所指出的,“现代社会进入了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之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空间规训的基本策略体现为对空间可见性的生产,使得空间中的个体“具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福柯,2003:225),权力最终“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福柯,1997:157)相对于福柯早期所设想的空间规训途径,社会化媒体将空间规训这种权力技术发挥的淋漓尽致人们不知疲倦地发表微博、更新状态、发起会话,过度地分享着自己的位置、行为、心情甚至一切私密的话题,在观看他人的同时,也在别人的目光压力下本能地调整着自己的网络状态,暴露自己与窥视他人成为一个同步交织的行进过程至此,“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霍尔•尼兹维奇(在空间可见性的生产策略上,社会化媒体并不是对可见性的简单试探,而是对可见性的直接描述和可视化表征如今,微博、微信、人人、陌陌、图钉、啪啪、密友、飘信等社会化应用纷纷转向移动终端,并且都内置了“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Service,LBS)功能当用户发布信息时,系统会附上个人所处位置的地缘位置信息,同时在电子地图上标注出来,再加上随手拍照所携带的空间实景信息,空间的可见性不仅被发现了,而且被可视化表征了微信的“附近的人”、陌陌的“地点留言”、人人的“人人报道”、遇见的“邂逅游戏”、群群的“随意群组”都是根据LBS技术来发现并激活可能的社交关系,不仅呈现空间的可见性,同时呈现空间关系的可见性,即空间被置于一张脉络清晰、有迹可循的LBS大网中,人们可以轻易地把握空间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结构关系因此,空间规训本质上体现为对空间的公开化、透明化、可视化处理,原本私密的、黑暗的个人空间被推向公共消费领域,成为资本、理性和权力可以把握的生产对象
三、国家资本:从“过场”到“去仪式”当前,空间规训超出了福柯早期所关注的空间形态,从政治空间或资本空间转向了对碎片空间的规训在福柯早期所设想的空间规训体系中,权力关注的是酝酿着重大事件或生产事实的空间形态,尤其是以监狱、学校、广场、纪念馆、流水线为代表的政治空间或资本生产空间,空间规训首先体现为对这些空间形态的可见性的生产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普遍而深刻的“过度分享”趋势中,那些原本躲在暗处的碎片空间开始进入资本和权力的关注视野,成为视觉和理性的把握对象,而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生产状态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碎片空间是一种常见的空间形态(弗里斯比,2003:11)在周而复始的权力、程序、仪式和直接的轮番改造下,人们奔波于工厂、教堂、广场、学校、医院、商场之间在空间与空间的连接处,甚至在同一空间内部,留下了各种形态的缝隙、空档和边角,这构成了常见的碎片空间其基本特征是黑暗性、私密性、动物性和反社会状态,这是资本生产的“盲点区域”,被历史抛弃,被商业忽视,被政治遗忘碎片空间本身没有价值,只是资本生产的“过场”,是一种“最卑微的、为传统史学所不齿的零碎、另类的事件、行当和人物”(由于碎片空间的可见性被发现,成为资本或权力的接管对象,人脉关系的重构行为因此进入一种生产状态,与之相应的空间实践呈现出智能化、匿名化、戏剧化特点随着LBS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连接和空间实践最终演化为一场被商业驱赶的消费体验在百度推出的“挚爱推荐”中,用户只要连续使用百度地图功能,系统便会自动记录个体的行动轨迹,并推荐生活路线最为匹配的人在某个合适的时候,百度自动启动地图导航,引导二人“相遇”显然,当空间成为资本征用的修辞资源,社会化媒体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崭新的空间经验其实,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两个陌生的空间实际上是偶然地、随意地、短暂地发生关系,这是一种松散的、易碎的、不确定的结构关系因为它们并非建立在某种强制性的理性与逻辑之上,而仅仅是感性的结合,是无意识的结合,是因为某种稍纵即逝的“缘分”走到一起除了对碎片空间的利用与开发,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规训过程甚至更加凌厉而彻底,开始对空间进行各种形式的“去仪式化”改造,其目的就是通过消解仪式来改写甚至消灭传统仪式所依托的诸多空间形式(当一切可能的空间形态进入社会化媒体的规训体系中,我们时代最后残存的隐蔽状态、黑暗状态、野蛮状态和非理性状态被摧毁殆尽,这在文化后果上引发了空间意义上的审美经验转向由古典性审美向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审美的转向古典性审美强调的是生命精神的超越性体验,核心是韵味、他律、永恒、距离、内容、静观、自然与天性(本雅明,1993:9-10)o审美不仅承认空间的黑暗性,同时积极挖掘黑暗本身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内涵当一个人生活在他人经验无法捕捉的黑暗区域时,为了抵抗认知遗憾,想象出场了,我们借助想象接近空间的不可见性正是在想象中,美学产生了,哲学产生了想象架构起了一条通往黑喑状态的认知路径,于是在文学或艺术史上留下了一幕幕关于距离、想念、残缺、别离等诠释空间不可见状态的美学诗篇一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相反,社会化媒体对碎片空间的过度开发与过度分享则撕毁了黑暗深处的美学价值于是,“审美”的意义改变了,强调的是一种弥合外部喧嚣与内心孤独的游戏冲动,并且转向了现代性审美经验所指向的浪漫、荒诞、反抗、震惊、自律、异化等消费话语,以及后现代性审美经验所诠释的游戏、拼贴、虚拟、破碎、仿拟、嘲讽等快感内容
四、空间规训从被动的观看到空间的流动基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空间规训极大地发展并延伸了福柯早期所设想的规训状态,并且制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后果,可以认为这是对福柯思想的一次批判性发展之旅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诸多空间规训事实已经超出了福柯规训思想的解释范畴,有必要对其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我们从与可见性生产密切相关的四个理论视角一一公共性、主体性、流动空间、资本的空间化进行论述首先,如果说在福柯那里可见性意味着权力压制和政治管制,社会化媒体则视可见性是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基质,是现实空间通往公共领域的基础性条件,空间规训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建构性的、祛蔽化的生存方式在福柯那里,作为权力技术的产物,可见性与公共生活无关,其目的就是通过对空间的设计和管理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然而,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生产,极大地解放了空间的社会性内涵和公共性特征,人们正是在“看见”的基础上重构人脉关系,并实现公共议题的构造显然,是“看见”而非“遮蔽”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基础,因为“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阿伦特,1999:38在丹尼尔•戴扬其次,福柯的空间规训建立在“观看”机制之上,其目的就是在空间意义上管理人、规训人、治理人,社会化媒体同样是通过“观看”达到空间规训的目的,但“观看”的方式、功能和意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对主体性的压制转向对主体性的替代性解放与拯救如果说福柯的“全景监狱”Synopticon依然是“少数人观看多数人”,社会化媒体则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另一种监视状态,即托马斯•马蒂森再次,在福柯的空间规训那里,权力运作的基本方法就是对空间进行静态化、封闭化、栅格化处理,以此隔断空间之间的社会学联系,而当前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流”worldstream状态,接踵而来的流动空间space offlows实际上愈加难以规训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之间总是动态的、感性的、游戏式的、戏剧化的发生关系,一种流动着的主体实践和空间结构被同步生产出来,曼纽尔•卡斯特2001:466-524所说的流动空间及其对应的空间体验在社会化媒体这里获得了最逼真的诠释随着手机移动服务的全面普及,再加上日常生活被进一步碎片化,主体实践的移动性愈加活跃,这势必带动了主体所处的“空间场”的流动一个空间总是动态地、实时地、不间断地与另一个空间发生关系,空间关系的搭建与重组呈现出一种流动化趋势Nike+、Sports TrackerRuntastic等能够即时记录用户的跑步信息、运动路线和沿途景观,这些数据实时上传到在线社区,一种流动着的人脉圈子和空间关系被清晰地标识出来人们在流动中征服了地方空间,空间的“流动化生产”构成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空间实践显然,“流动”空间并非建构了新的封闭空间,而是铺设了一个更加难以规训、难以管理、难以约束的空间结构和生产状态,这与福柯所设想的空间规训状态相去甚远最后,就空间规训本质而言,福柯强调政治权力的空间化过程,而社会化媒体则指向资本权力的空间化过程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表征、碎片空间发现与流动空间生产,基本上是由资本欲望和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一场消费革命,权力正是在空间的资本化过程中无限延伸与福柯所设想的空间规训后果不同的是,社会化媒体深刻地改写了整个社会的空间体验与空间结构,即从中心空间到边缘空间、从静态空间到移动空间、从生产性空间到消费性空间、从线性结构空间到拓扑结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当碎片空间走出了其原始的黑暗状态,成为资本竞相争夺的生产对象,空间的功能和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一一从黑暗性向可见性扩张,从动物性向社会性扩张,从反社会状态向社会状态扩张这使得原本模糊的、瞬间的、偶然的黑暗空间被重新识别和利用,最终改写了空间的物理属性和文化意义比如,传统的卧室空间是绝对的隐私之地,处于权力监管的黑暗之处,其功能就是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产出的封闭空间然而,当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服务进驻卧室空间,人们入睡、起床前总会本能地玩弄手机,现实生活正接受着“再仪式化”的仪式再造过程,这使得被窝里的经济学意义被发现了于是,原本象征反社会状态的黑暗空间被资本接管,开始向社会状态开放,卧室空间的性质和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偏移和改变。
 个人认证
个人认证
 优秀文档
优秀文档
 获得点赞 0
获得点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