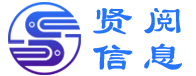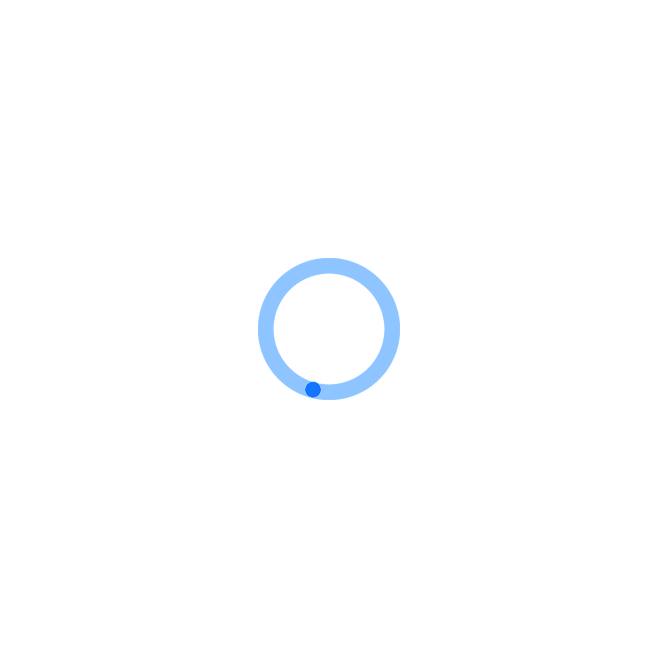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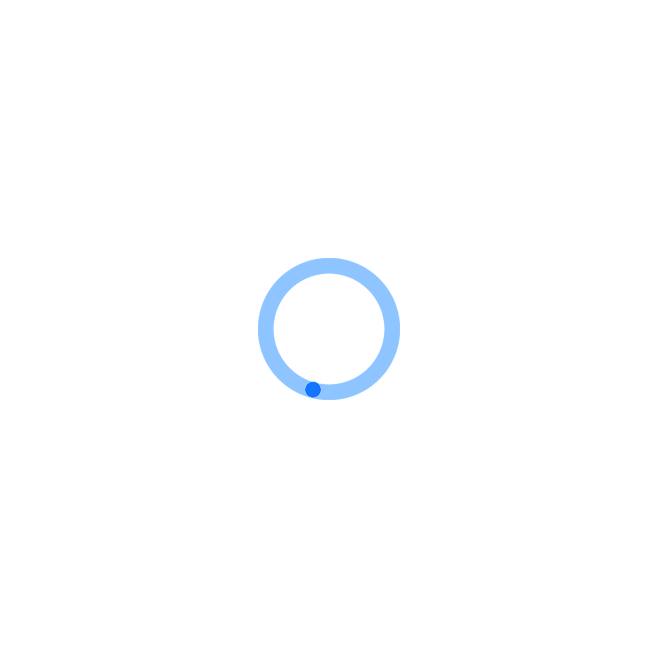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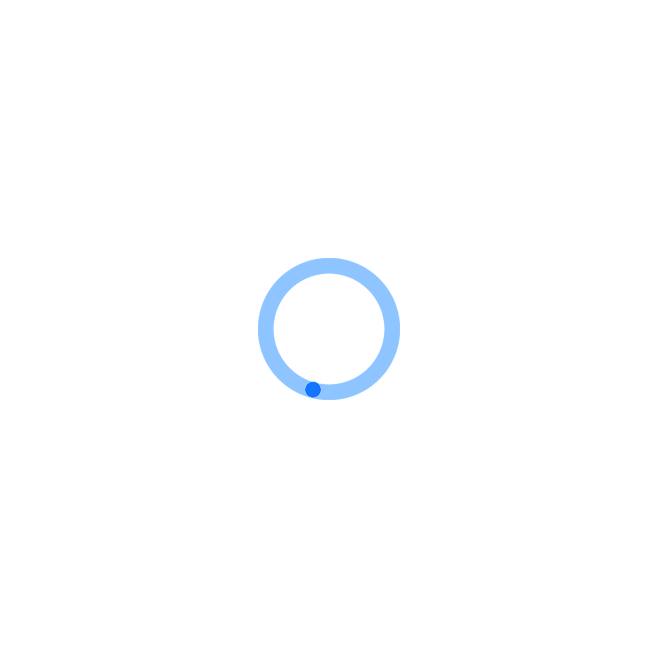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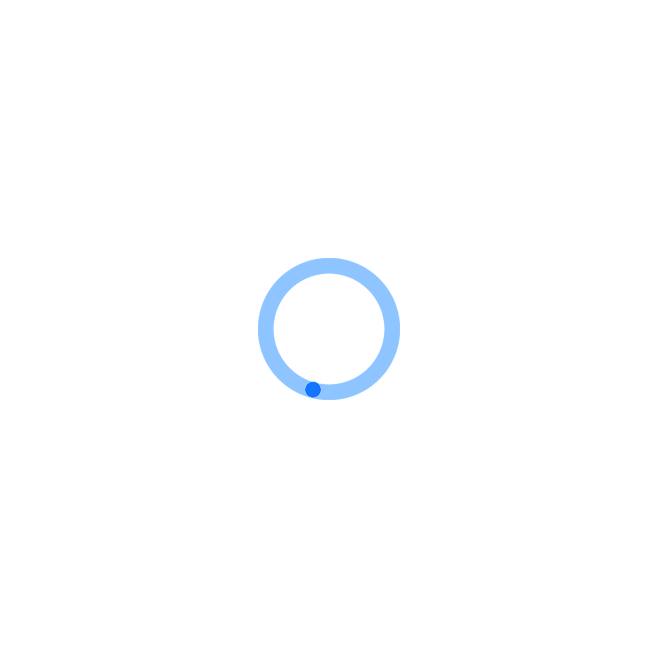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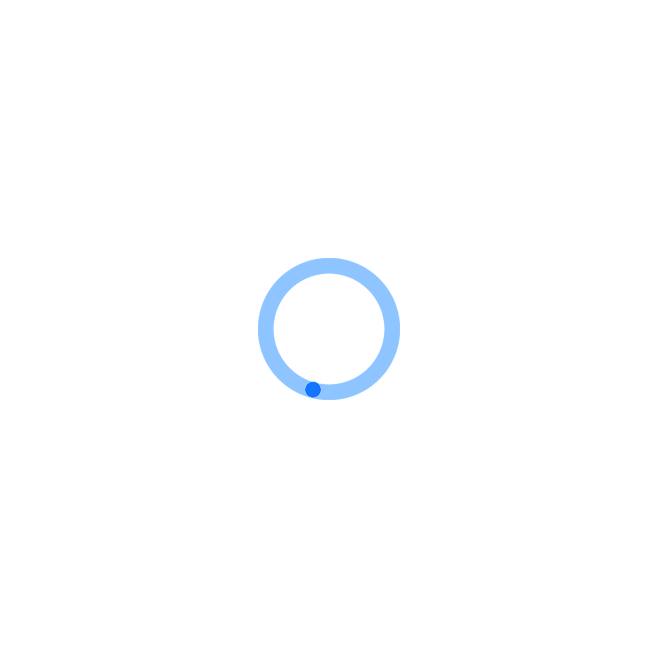
还剩3页未读,继续阅读
文本内容:
《班定远平西域》中的以今翻古班超、文学创作《歌剧团原平西区》以下简称“班”是梁启超1873-1929为日本横滨大同学校音乐俱乐部创作的一部粤剧该漫画于1905年8月至10月在新小说中连载,署名为《曼殊室的主人》该剧内容取材自《后汉书》中“班梁列传”一篇内班超公元32—102的部分,讲述的是汉代名将班超出使西域平定边疆的故事全剧正文共分“言志”“出师”“平虏”“军谈”“上书”和“凯旋”六幕第一幕前有“例言”,第六幕后附有乐谱和粤语释文在“例言”中,梁启超说明“此剧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前人关于该剧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其纳入对梁启超戏剧活动的总体考察,分析梁启超的戏剧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如1920年,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开篇写道“翻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盖以今语读古书,义应如此其实不过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化而已”从翻译视角来看,本文通过《班》剧与“班梁列传”文本的对照,探讨《班》剧的成因以及梁启超在其中对史书做出的增删与改写,同时联系晚清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梁启超的个人思想来分析这些改动背后的动机,以期为《班》剧及晚清时期的历史改编戏剧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方法
一、“有呈微言,吾耻其言”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晚清时期的中国受尽列强欺凌,风雨飘摇任公虽身处异国,却仍心系维新之事1902年,正是他“破坏论”思想最为激进之时当年他不仅先后创办《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宣扬维新思想,更是写就《新民说》,继续着关于开启民智的思考在《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他讲到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辱,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而我国民百世弥天之大辱也!”到了1904年,梁启超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显然与他1903年游历美洲大陆后政治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有关尽管在写“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之时他对于“中国民族之不武”的观点表现出了些许松动,但总体上却还是认可的,那时他认为,张博望、班定远也只是他从浩瀚历史中仅能找出的一二“特例”而已然而,到了1904年《中国之武士道》一书的“自叙”中,他对于此观点表现出了彻底的否定,慷慨激昂地自陈“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目光复归传统之后的梁启超逐渐开始认为,尚武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一部分“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据“班梁列传”中记载,班超生于史学之家,父亲和兄妹皆为《汉书》的修纂者他虽博览群书,却不甘于从事文职,有建功西域之志他当过兰台令史,但因为过失而被免官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公元28—75)派窦固(一公元88)出征匈奴,班超投笔从戎,作为假司马随行,在匈奴立下战功,继而被窦固派遣跟随郭恂(生卒年不详)出使西域在都善国,班超凭借自己的勇武与韬略,歼灭了匈奴使者,使得在匈奴和汉朝间摇摆不定的都善归附了汉朝随后的20多年间,班超先后平定50余国为褒奖其功劳,汉明帝封他为“定远候”班超到了暮年,思乡心切,上书请还,但过了3年都没有回音;于是班超之妹班昭(公元45—116)再次上书,皇帝被感动,下旨召班超回朝然而,由于已患重疾,他回朝仅一个月便与世长辞而班超在西域的继任任尚,由于没有听取班超临走时的告诫,致使5年之后西域之乱又起之后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言,“匈奴之患,遂与汉代相始终”(对于班超平定鄱善、莎车、疏勒、焉耆、姑墨和龟兹等国的故事细节,无论是“班梁列传”还是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都有悉数记录但到了《班》剧中,梁启超只选取了都善国一个例子,并且调整顺序,将其由最先平定的国家改为最后一个如他在“例言”中所说“定远在西域之业本发端于都善,以次削平诸国,今移都善于最后,实与史文显违所以必如此者,缘其他武功万不能多演,而都善一役最合于剧场兴味若叙都善而不及其他,又大失精彩”(然而,除了因为客观条件而不得不作出的改动外,梁启超在有的具体细节上也同样进行了增删或改写因此,史书上的故事,在《班》中并未完全以原貌呈现:班大将军在异域建功立业的故事最终被改造成了一部宣扬“尚武精神”的通俗精神教育读本
二、班超的宗旨与《黄粱梦》“班超”对他的志域背景的影响与史书相比,班超的正面形象在《班》剧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首先,《班》剧将“班梁列传”中的故事掐头去尾,对班超出使前因过失被免官、回朝后不久便病死以及匈奴之患伴汉代始终的事实隐而不表梁启超在“例言”中说道“此剧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而所尤重者,在对外之名誉,故选班定远为主人公”(再者,班超求取个人功名的志向在剧中也转变为报国之志历史上的班超非常敬仰张骞(前164—前114)和傅介子(一前65),“班梁列传”中写到他经常感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第一幕“言志”中,班超开场的引唱“万里封侯未足多,天教重整汉山河何当雪耻酬千古,高立昆仑奏国歌”(除此之外,“言志”中班固(公元32—92)与班惠对话的添加,也从另一面让班超这种略显极端的重武轻文的态度得到缓和其实,原文中对班固并没有重笔描写,只是在介绍班超家庭背景时简略提了几句然而,剧中他成为了一个“文吏”的化身班超开场时即说自己“性厌丹铅,腹娴韬略”(
三、从“开圣主”到“德主”班超平定西域的故事前后跨越30余年,期间汉朝的皇帝也更替了三代但无论在位的是何人,他们都是专制皇权的代言,虽然不可或缺,但并非举足轻重有趣的是,经过种种改写,“班梁列传”中似乎全程只负责发号施令的专制皇帝形象,到了《班》剧里摇身一变,成为了爱民惜才的开明圣主梁启超自1903年游历美洲大陆后,放弃“破坏主义”而转向“开明专制论”,《班》剧作于1905年,正是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时期可以推测,很可能正是因为思想上的转变,才导致他在《班》剧中对原作进行增删,来塑造一个更为开明的君主形象如此一来,以班超为典范的“尚武精神”,便被置于“开明专制”的背景之下,君主对于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出来按照“班梁列传”中记载,“(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惧使西域”(此时在剧中出场的汉和帝,先是通过“承先皇将江山命孤执掌,十三年勤宵肝日戾不遑”
四、《班》“从军谈”“俗曲新用”之举?黄雪敏在“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分析”一文中指出,趣味是梁启超戏曲美学的核心内容,“梁启超的趣味美学在继承了前人对趣味的重视的基础上,又极其强调趣味的实际作用”(剧中粤语的使用,集中于“平虏”和“军谈”两幕,“平虏”中匈奴钦差与随员的对话,以及“军谈”中士兵的对话和对唱,基本用粤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匈奴钦差登场时一段插科打浑,台词中融合了粤语和英语(钦差唱杂句)我个种名叫做Turkey,我个国名叫做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Family,地下国王都系我口既Baby今日来到呢个Country,(作竖起一指状)堂堂钦差实在Proudly可笑老班Crazy,想在老虎头上To play(作怒状)叫我听来好生Angry,呸,难道我怕你Chinese难道我怕你Chinese而钦差随员的唱词中,则同时夹杂了粤语与简单的日语:(随员唱杂句)才^系匈奴口既副钦差,(作以手指钦差状)除了7,就到我工子彳(作顿足昂头状)哈哈好笑^十也闹是讲出夕彳叫老班管口既来廿彳彳巨都唔闻得才^口既声名fl〜廿夕、:/力J真系才I八力咯才7〜这种语言杂糅的行为,不仅新奇有趣,而且极富韵律感左鹏军认为,“从中可以推测梁启超创作时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用意,也可以推测这种独特语言形态可能造成的特殊表演效果”(尽管如此,“军谈”一幕中士兵的往来对唱以及“俗曲新用”之举,也还是为舞台增趣不少此幕描写士兵在一起唱歌谈心,表达心中的豪情壮志以及对国家的热爱在士兵甲以《龙舟歌》为曲牌唱完一首雄浑壮烈的新作之词后,士兵乙表示要用俗曲《梳妆台》来唱“从军乐”,对此甲表示质疑,说《梳妆台》是“靡靡之音”,担心“唔但系振唔起尚武精神,反变成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睇见近来有好多文人学士,都想提倡尚武精神,或做些诗,或做些词但系有腔有调,又唔唱得,耍口黎何用睹又有的依著洋乐,谱出歌来,好呢有错系好但洋乐口既腔曲,唔学过就唔哙唱,点得个个口甘得^去学彳巨呀独有你呢几首“梳妆台”,通国里头,无论大人细蚊,男人女人,个个都记得呢个调,就个个都会唱你呢只歌据我睇来,比大同音乐会学个的野,重好得多哩可见,“俗曲”作为旧形式的一种,倘若利用得当,是非常有利于以一种通俗有趣的方式宣扬“尚武精神”的,这便是前文所说梁启超“强调趣味的实际作用”的再次体现当然,《班》剧的趣味性,还不仅仅体现在舞台的表现形式上,从剧本的宾白和唱词来看,梁启超并没有将故事彻头彻尾地置于汉代的背景之下,而是利用时空的交错造成的滑稽感,不时提醒着读者剧情与现实的关联汉朝与晚清相去近两千年,但我们在剧中却经常能看到晚清的社会现状例如“出师”里皇帝唱白中“四百兆同胞血统”显然说的不是汉代的情况,而“小武西装军服”、徐干“在陆军大学堂卒业多年”、匈奴国随员喝“威士忌”以及汉营士兵“饮酒食面包”等场面的出现,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平虏”中甚至出现了“横滨领事”和“中国皇太后”这样明显的指涉同时,在“军谈”中,梁启超更是借士兵所作“龙舟歌”中“谁想太平日久人心倦,士气民风日日趋文弱”、“枉被泄沓庸臣弄国权,睇我口地军人唔值半文钱”、“今日呢帮插手要我居留地,明日个国出头又要占我实力圈”(然而,这样做的目的,既不仅仅是为博读者或观众一笑,也不是为了提醒他们现实的惨状,让他们徒增伤感,而是希望他们在认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激励和鼓舞,重新唤起国民内心的“尚武精神”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会对“班梁列传”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军谈”和“凯旋”两幕大写特写他让班超在“言志”中早早就唱到“我祖国,大中华,惟天骄子”(尽管梁启超坦言在有限的时间出演新剧“实非力所逮也”,但《班》剧中所展示出来的舞台趣味与新意,却正是梁启超尝试改良旧剧所带来的结果他的这种尝试,不仅仅源自于个人的审美趣味,这种革新背后的指向,更加反映出他以启蒙为目的的现实关怀正如夏晓虹所言,“若要为《班定远平西域》在中国戏曲史上定位,最贴切的评语还是来自梁启超本人一一’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也”
五、《班》剧的语言特征蒋林曾经在分析王晓平、郭延礼和王向远三位学者对“豪杰译”的界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豪杰译”是指明治初期的日本译者,为了思想启蒙或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常常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任意增添、删减,甚至改写这种翻译的方法被时人称作“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的束缚,任意改动原作的翻译方法如果按照本文开篇提出的观点,《班》剧视作梁启超以“班梁列传”为底本翻译而成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将上述定义的适用范围由“外国作品”加以扩展,将“以古翻今”或“语内翻译”的作品纳入研究范畴通过对《班》剧的层层分析可知,梁启超在以白话翻译古文的过程中,有意对原文进行了改动首先,为了在本国历史中寻找理想的“尚武典范”,他刻意隐蔽了一些不利于理想形象构建的负面情节,并将班超个人的功利之心转化为宏大的报国之志,使得他的正面形象更加凸显;其次,为了配合自己的“开明专制论”,他通过人物对话的增添和故事情节的调整,将原文中形象模糊的封建帝王塑造成了一位仁德兼备、崇军尚武的开明君主;最后,考虑到当时演出的具体环境和受众,他从语言、音乐和内容等多方面着手,增加了剧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以便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这些改动中既有增删,也有改写,都是围绕着启蒙的目的而进行的,体现出了梁启超希望通过提倡“尚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的动机由此观之,《班》剧的翻译,完全符合晚清“豪杰译”的特征这个新的角度,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文本产生过程中的各种转换及其背后的种种关联因素,不仅可为研究晚清时期取材于史书的戏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进一步丰富了“豪杰译”的内涵。
 个人认证
个人认证
 优秀文档
优秀文档
 获得点赞 0
获得点赞 0